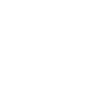随 笔
说到“吃喝玩乐”似乎与清华附中的教育无关,在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年代,这四个字怎能谈起。也可能是个人到了应该全面的、创造性的“吃喝玩乐”时候,回忆起母校这方面,对我终身还真是有影响。
先说说“吃喝”。
1963年9月刚入学的那个月,记得伙食费是5.95元,是开学时交的。我妈那时说伙食费较低并嘱咐:学生嘛就应该清苦些。但是真到了吃饭时,感到与家里差距太大了。有一次早饭,解建华同学对我说,若没有咸菜这窝头是无法下咽。我当时马上反应是:就是咸菜也给得太少了,若计划不周真难以作到一口窝头一口咸菜。但很快伙食费逐步在上调,尤其是到了初二时每月已到13元。后来才知道,保证学生每月有一定量的肉食(每周三两肉?),保证伙食水平高于同类学校,是万邦如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
特别是酸奶事件给了我很深印象和营养重要的启蒙。好像是在初二下学期,食堂来了个卖酸奶的“个体户”,一时排队买瓶装酸奶的队伍与多数人的议论纷纷搅合在一起,于是,队排得越来越短。班里一个坚持喝酸奶的同学特意向大家解释:从小体质差,需要补补营养。我怕所谓影响不好,顾左右而偷偷买过两次。啊!酸奶加馒头的美味太诱惑人了,但是,不行啊,忍着吧。这种状况校领导得知后由顾涵芬老师召集各班支部干部在其办公室开会(二楼),大意是说这种情况是同学思想片面的体现,讲了吃酸奶有益于同学们身体健康的道理。尤其是顾老师最后呼吁“大胆的吃吗!”,这句话印象太深了,思想解放了!长队又排起来了。
回想一生无论在何时何地从未在这个问题上有“左”的言行,这与在附中注重学生营养的实践与教育有关。以至于几十年后,一次在某公司打工时,领导作出取消经理餐的决定,在中层会上我从脑力劳动更需要高蛋白食品角度提出意见,不但未得到批评,反而总经理底下对我讲:你讲的对,但董事长的决定,我也没有办法……云云。
再谈谈“玩乐”。
清华附中的“玩乐”是高层次的,实质是对美育的重视。那时母校不但对“德智体全面发展”不折不扣的全面贯彻,校领导对美育的重视和实践,现在无论怎么高的评价都不过分。我想在重视所谓美育的当前,即使在艺术类中学里,也难有像吴成璐,王玉田这样水平的艺术老师,何况一般中学。这方面我们得到了终身受益的熏陶:高质量的美术,音乐课,对管乐器、弦乐器的培训等等。集中体现在小东方红的演出上,尽管是少数同学参加,其对全校同学艺术修养影响是巨大的。
由于从小的环境条件,到初中时我基本还是个音盲,对乐器的接触更是无从谈起。我生来第一次看到小提琴演出是在附中1963年开学典礼的大会上,在清华大礼堂由附中新来的音乐老师(记不得姓氏了)独奏,王玉田老师钢琴伴奏,曲子是“唱支山歌给党听”。它给了我对这种乐器的神秘感。初一时,有一次到姜岁宁老师家,她拿出小提琴即兴演奏了一段曲子(我当然听不懂),姜老师演奏时的形态至今脑海里留有印象。从那时起,对这种洋乐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虽然音乐课上没有对小提琴的教学,但是学校在课堂上开设了二胡(现在想起来像是京二胡)课,每二人一把。弦乐是相通的,这为我后来敢于拿起小提琴玩乐,打下了好的基础。尤其是我因条件所限,不懂如何正规练习小提琴,但是我采用二胡的拉法(食指切弦法)拉提琴,也达到了自娱自乐的水平。后来由于忙于生计和自认水平太低无法提高,就放下了。在退休后,有人建议我买钢琴练习以防止老年痴呆,且不说家里加一立式钢琴的地方使我伤脑筋,就是其声响对街坊邻居的影响恐怕要顾及。于是就又捡起了小提琴,更换高一档次的硬件再加一弱音器问题全解决了。现已接近当年水准,自娱自乐的需要和对老年痴呆的高度恐惧,我会坚持拉下去。
对乐器的接触不但使手指和脑的活动有益于身心健康,也对音乐欣赏水平的提高有益。当我有时在现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听所钟爱的室内乐时,那种享受和感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
清华附中的几年(包括文革期间)经历,对我一生道路走向的影响是全面的,受益感激不尽。